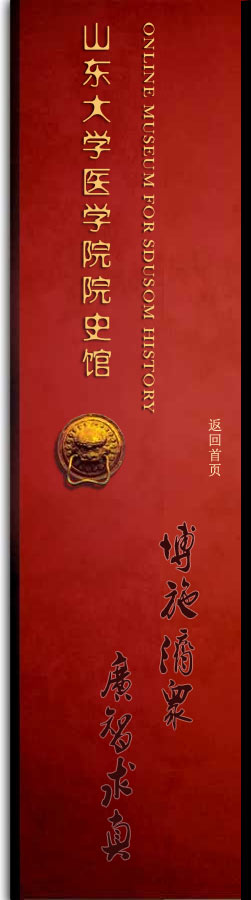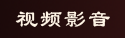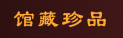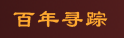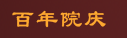五、名 人 逸 事
五、名 人 逸 事首页 > 文史资料 > 名人逸事
|
近代美国北长老会在登州居住 |
|
如所周知,在自19世纪初以来的人类近代历史上,欧美各国大批基督新教传教士奔向世界各地,源于基督教内部福音复兴运动即“第二次大觉醒运动”(The
Second
Awakening),这一运动把原本局限于欧美一隅的宗教变成了遍布全球的普世宗教;19世纪蔚为壮观的海外宣教浪潮,既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结果,又是使基督教变为遍布全球普世宗教的强大推动力。 从根本上说,基督教19世纪的大规模海外宣教运动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为西方列强的全球性扩张和基督教的海外宣教运动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人类社会处在这一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世界各地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一样,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发展也是极端不平衡的。毋庸置疑,19世纪各国基督新教的海外宣教运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股强势文化浪潮,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但这一浪潮却与各国政府以及各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并没有直接关联。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们奔赴世界各地,不是受政府或商人派遣,承担为政府或商人服务的使命,而是出于宗教信仰,主动要求或愿意并经所在教会批准,到非基督教国家的人民中传布基督福音、上帝之爱。他们是为上帝服务,为信仰献身。 在这样的历史浪潮中,地处世界东方的华夏神州人间仙境登州蓬莱,无可置疑而又有些奇妙地卷入了这一历史大潮之中。 2006年春夏之交,笔者在参加蓬莱市《蓬莱文史通览》编纂研讨会期间,曾听到近代西方基督新教传教士“云集”人间仙境的说法,由于当时对这段历史的无知,心下颇感愕然:有什么证据说西方传教士“云集”蓬莱?大家都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规定登州对外开放通商,但不久即因当时港口和商贸条件而改为烟台,如果说开始传教士们只知道蓬莱开港迫不及待而来,后来了解了真正开港的不是蓬莱而是烟台,还会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吗?如果真是这样,原因何在? 带着上述疑团,笔者贸然接受了搜集近代到登州传教士资料的任务。经过近一年的不断搜求,虽然萦绕于心的迷雾渐散,但同时又为一些地方网站、各种报刊上似是而非的说法所苦恼。历史研究的真谛首先在于弄清史实,舍此便无所谓研究。本着这一宗旨,不断求证至今,终于不能不佩服当初“云集”说的高明,同时也大致揭开了西方传教士何以会“云集”蓬莱的原委。 查近代到登州安家落户的西方基督教组织,有美国南部浸信会和美国北部长老会两个差会。美国南部浸信会据称是“美国最大和最具活力的新教教派”(小海亚特:《圣使荣哀录——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3),它的山东差会,也是基督新教在山东建立的最早的差会,到蓬莱的时间也比长老会稍早一点。但是,从后来基督新教在山东的工作和发展情况看,它的事业无论在哪一方面,特别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都远不如美国北长老会。美国北长老会,虽然来山东和登州不是最早的差会组织,但发展迅速,辛亥革命前已经是山东最大和最有实力的差会组织了。由于笔者有些美国南部浸信会的中英文史料尚未搜罗到,现在还无法罗列出有根有据的到登州的人员名单,有待今后继续努力,这里先将美国北长老会来登州的人员详列于后,并就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的重要事迹加以考释点评,以期为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山东地方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可靠的线索。 美国北长老会差会始建于1861年夏,是年5月盖利夫妇和丹福斯夫妇到登州,6月倪维思夫妇从宁波来,均暂无居所,在先到登州的南浸信会牧师海雅西家里落脚,是为登州长老会创设之始。但就在这一年,丹福斯夫人病故,丹福思返回美国。1862年,梅理士夫妇从上海来加强登州力量,结果盖利染霍乱不治身亡,夫人返回美国。翌年,倪维思陪夫人返美治病,登州仅存梅理士夫妇二人。1864年,郭显德夫妇、狄考文夫妇从美国来到登州,年底郭显德夫妇迁烟台。可见,登州长老会数年间一直处在艰难挣扎之中,并没有稳定的组织和人员。它的兴旺发达,是在狄考文办的学校成功之后。据初步不完全统计,从1861年盖利、丹福斯两夫妇来,截至日本大举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美国北长老会先后来登州的正式工作人员,确实有据可查居住至少近一年以上者即达86名之多,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前特别是1904年之前到登州来的,1904年以后来的不足10位。这一数字,不包括每年夏天到这里来度假避暑的传教士及其家属,也不包括在登州出生和生活的传教士子女。同一时期同一类型到烟台的,确实有据可查者仅55人。自1880年代起,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以后,基督教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大城市转移,登州海边小城一隅之地,19世纪的交通极为不便,仅美国北长老会一个教派,为什么就有这么多的传教士先后“云集”这里? 从现已翻阅到的早期来登州和山东的传教士们自己写的保留至今的资料看,虽然在传教士初来的10多年间,一般民众因为“洋鬼子”是在清政府战败后被迫允许他们来的,绅士们由于“洋鬼子”传的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大相抵牾,最初表现不友好乃至希望把他们赶出去,但当时无论当地政府还是民众,又都清楚中央政府已经和谈立约,自始就给了这些不请自来的“洋鬼子”生活和活动的空间。比如说,美国南部浸信会的海雅西1861年初到蓬莱时,经知县允许租赁了城北门附近的一家闲置的当铺;是年夏天北长老会的盖利夫妇和丹福斯夫妇到登州时,蓬莱知县为他们指定了城东门附近的东大寺和寺后的姑子庵作居所,稍后倪维思夫妇又租赁了近水门处的观音堂;东大寺及姑子庵后来也一直归长老会使用,并没有像教会中人所担心的那样,“官指之地,日久年深,官府可以收回”(连警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37年版,第160页)。对比第一次鸦片战后近20年间,广州绅民和官府不许外国人根据条约进城,以及福州有传教士租住庙宇被官绅赶走等情形,我们不能不惊叹当时蓬莱官绅民众朴素的理性、正直、仁慈和宽厚胸襟。蓬莱官绅民众在19世纪60-70年代对外来事物的态度,充分显示了蓬莱文化的巨大包容性。 事实上,蓬莱官绅民众所展示的蓬莱文化的理性、正直、仁慈、宽厚和包容,也是胶东文化的特征之一,只不过蓬莱在这方面显得更典型罢了。史载郭显德、狄考文到中国第一站是在上海登陆,接着他们便和英国浸礼会的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夫妇等人换船直奔烟台。结果船在大约威海至成山一带海面迷失方向搁浅。时值深夜,不仅风大浪高,且阴云密布,漫天飞雪,一众人等弃船涉水上岸,翻山越岭好容易找到了一个村庄。其时天快亮了,大家到一户人家门前敲门。良久,一位老汉开门出来,“老人不懂外国话,众人不懂中国话。彼此手势之下,老者便知就里,又见众人上无风帽,下无棉鞋,衣服尽湿,满身冰雪,即知必是船破得救,前来求助者。初反长毛之后,谁敢照应毛子?乃于此冷意拒绝之时,忽见韦廉臣怀中抱一小孩,此小孩闭眼缩拳,浑身冷战,迨将冻毙,乃大生恻隐之心,放舒冷脸,忽翻笑容,大开其门,招之令众人入”。然后又把家里没起床的人都叫醒到别处去,弄草烧炕,煮饭招待。在得知这伙人要到烟台后,还派人到烟台送信,三天后有英国小炮艇来,才把他们接走(详见连警斋编前揭书,第31-32页)。这一事实说明,胶东老百姓已经朴素朦胧地把外国侵略者和一般外国人区分开来了。传教士把他们这次得救归功于上帝,认为是危难时刻不停祷告感动上帝,上帝救了他们。事实上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这位仁慈、宽厚有着朴素理性的胶东农村老人。据鸦片战争前到过山东沿海的西方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郭士立(Carl Friedrich Augustus Gutzlaff,又作郭实腊、郭施拉、郭甲利)记述他的亲身经历说:第一次在中国沿海旅行时曾登陆胶州,“发现山东本地人比南方各省居民正直,尽管南方人极其不敬地把他们看成是下等人”。但理性、正直、仁慈、宽厚和包容并不等于柔弱可欺。郭士立第二次中国沿海旅行时在威海卫登陆,经过观察对比,他认为胶东人“如果给以很好的训练,他们会成为优秀的战士,因为他们是我见到的所有中国人中最勇敢的” ( 法思远主编、上海广学会1912年出版的《中国的圣省山东》——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P.177-178)。 狄考文传记的作者费舍,是狄考文大学和神学院的同学,后来担任美国汉诺威学院院长,十分关心国外布道事业,两人长期通信。狄考文去世后,他用两年时间阅读了大量狄考文生前的日记和各类信函,写成狄考文传,在谈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登州所遇到的情形时,说“登州人对外人的态度,确实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甚至直至今天的态度要友好一些”(费舍:《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P.71)。他这里所说的“登州人对外人的态度”,指的是狄考文刚到登州不久当地人对外人的态度,而他所说的“今天”应为写作此书时的1909 或1910年,前后相差40年登州与其他“许多地方”对外人态度的比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这时清政府已经推行新政改革业近十年,在全国范围内主动学习西方,很多省份都自辟商埠对外开放,山东的济南、潍县、周村,就是1904年由山东巡抚周馥联衔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申请对外开放,经清政府批准辟为商埠的。 除了上述原因,近代美国传教士“云集”登州的另一因素不可忽视,甚至可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狄考文在这里相对宽松和谐的中外交往环境中,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而且“几乎无疑是19 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 (海亚特前揭书,第140页),成功教育家的名声在传教士圈内尽人皆知;他花费心血编纂的《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即人们平时所说的《官话课本》),是当时外人学习汉语的最好的入门书,他本人因此被来华传教士誉为北中国传教士们“学习汉语的一本大书”(法思远前揭书,第190页)。在狄考文离开登州前,很多传教士都是到这里学习汉语和见习传道的。 下面列出86位(邓乐播夫人未单列)近代在登州居住、学习、生活和工作过的美国北长老会成员,并对有关重要事迹进行简要考释点评。尽管由于有些资料阙如,还不尽完善,但这些人员名单及有关重要事迹的考释点评,却是在对当时及后来中外人士留下的第一手资料,或根据第一手资料编著的中英文著述的仔细反复翻检爬梳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订正了前此不少似是而非的史实错误,也指出了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冀望对蓬莱乃至山东地方史志研究编纂工作能有所裨益。为达目的,尚祈方家不吝补遗正误。 由于这里所列到登州的美国北部长老会人员及其事迹所据资料非常集中,以下叙述除非特别重要的一般不详细注明出处,而在文末列出所查参考书,以避免过多重复。同样,因为以往有关不确不实说法牵涉的地方网站、报刊甚至专业期刊太多,也不便一一注明,敬希谅解。 盖利牧师(Rev. Samuel R. Gayley,又作干理、干霖、干雷) 1857年来华,先在上海(上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即辟为通商口岸),1861年5月携夫人与丹福斯牧师夫妇一起到登州。初在先期来登州的美国南浸信会海雅西(J. Boardman Hartwell,又作海大卫,1861年1月到登州)牧师家落脚,随后搬入东大寺,10月租住观音堂。这一年下半年及1862年上半年,到各处乡间传道,最远一次曾和南浸信会的海雅西结伴一起到了莱州,收了一名叫宁中的基督徒,为莱州乃至山东第一位基督新教教徒,但这名教徒后来并没有列在登州长老会名下。 盖利牧师夫妇与丹福斯牧师夫妇1861年夏组建的美国长老会登州差会(亦称长老会公会)是山东最早的长老会差会。 这里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南北失和,爆发了内战,南北各自前程未卜,但南部浸信会和北部长老会的传教士们,尽管教派及所属地域不同,却在基督信仰的大前提下精诚合作。这种情形只能从宗教学的角度予以解释。 1862年7月,盖利牧师去烟台迎接来登州的梅理士牧师一家。盖利夫人与梅理士乃亲兄妹(一说为亲姐弟),梅理士的小孩在烟台感染虎疫(虎,音kǔ),路上传染了盖利。结果,盖利未及到达登州,即不治身亡(虎疫,俗称霍乱)。 盖利夫人(Mrs. Samuel R. Gayley,教内人称盖师母、干师母) 美国纽约人,1861年到登州,盖利牧师去世后,随即返回美国,1863年再嫁了爱尔兰好莱山的安德鲁•布朗(Androw Brown)牧师, 1894年11月13日在美国密执安州安阿伯市退休,那时她的孩子们正在这儿求学,她与前夫留下的唯一的孩子,成人后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纯文学教授。 丹福斯牧师(Rev. J. A. Danforth,又作但福斯、旦福斯、旦富德) 1859年底或1860年初来华,先在宁波学习语言和见习传教,1861年携夫人与盖利牧师一家一起到登州。是年9月,夫人病故,年底返回美国。 丹福斯夫人(Mrs. J. A. Danforth,教内人称丹师母、旦师母) 1861年到登州,当年虎疫病故,经交涉,允葬水城附近海边岗地,是为美国北长老会也是近代基督新教在登州去世的第一位外国宣教人员。 倪维思牧师(Rev. John L. Nevius) 美国纽约人,1954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宁波、杭州等地传教,期间并到日本传教8个月。1861年6月到登州,1871年迁烟台,1893年在烟台寓所病逝。 倪维思一生传教之余,勤于著述,除了在当时出版的英文版《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经常发表文章外,还有英文《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and its Inhabitants)、中文《两教辨正》等著作问世,对研究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中国文化以及不同文化比较,极有价值。此外,他还精于园艺,曾将美国苹果等引入烟台嫁接成功,后来著名的烟台苹果,即由此而来。 倪维思夫人(Mrs. Helen S. C. Nevius,时人称倪师母) 1861年到登州,1871年随丈夫一起迁烟台。1893年丈夫去世后,继续在烟台、登州等地传教,在中国传教、教学57年,1910年去世。 倪维思夫人除传教和在教会学校教学之外,业余时间也勤于著述,写有不少早期到山东特别是登州的基度新教传教士中文小传记,以及长老会早期登州、烟台传教史,但可惜的是这些中文著述现在已难见到。其中较著名的《传道模范倪公维思事略》(上海美华书馆,1897版,简称《传教模范》),《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中有大量引述。英文著作Our life in China (New York: Robert Carter and Brothers, 1868),介绍他们夫妇到中国初期各方面的情况,但现在国内已难见到。另外,在倪维思去世两年后,倪维思夫人亲自撰写的《倪维思传》(Helen Sanford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New York : Fleming H. Revell, 1895),则描述了他们夫妇截至1893年的在华经历和事业,如果能读到这本书,或可帮助我们搞清楚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早期在登州、烟台一带的活动情况。 倪维思夫人在登州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于1862年冬季,创办了登州女子学堂,是为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开登州和山东女子教育之先河。女子学校中“女学生放大脚,穿踹裤(即不扎裤腿)”,惊世骇俗,于改良社会风习,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民众素质,有前驱先路之功。晚清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曾倡行放足,但未得推行。清末新政时期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废除缠足陋习,辛亥革命后进一步大力推广,但事实上直至20世纪20-30年代,也未能禁绝缠足。今天我们在很多地方还能见到80-90岁的老太太,有不少都是小脚,就是明证。可见风习的改变何其缓慢艰难,由此也可以想见早在19世纪60年代传教士倡行放足会有多大阻力。 神学博士梅理士牧师(Rev. Charles R. Mills D. D.) 纽约州吉尔福德(Guilford,N. Y.)人,1856年10月携妻子与盖利夫妇等一同来华,翌年2月抵达上海,因不适应上海的气候,1862年7月到登州,自1865年起至1895年去世,一直担任登州长老会负责人。 有人说:“美国长老会是山东基督教差会中最大的一个。在那些老传教士中,狄考文像一个大家族的长辈似的领导着登州地区的美国长老会”。这显然是不对的。梅理士的名气虽然没有狄考文大,但却是登州美国北长老会继倪维斯之后的负责人。 自梅理士到登州后,与继来的郭显德、狄考文三人,与当地人渐趋融洽,随着人们对他们各自性格及行事方式的了解,分别送给了他们一个绰号。梅理士牧师为人处事谦和恭谨,身材清瘦修长,人送绰号“梅花鹿” 梅理士在登州传教34个年头,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的最大贡献是: 一、1874年与继室夫人梅耐德共同创办了登州启喑学馆,将西方现代聋哑人教育引入中国。 登州启喑学馆是山东也是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1898年迁烟台。 二、引种美国华生获巨大成功,花生、花生仁、花生油遂成为近代山东重要出口商品,对山东农副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创办聋哑人学校一事,尽管以往有的较权威的大型统计资料记述有误,但现在学界已经公认,毫无疑义,毋需进一步澄清。引进美国花生一事,似尚有争议,有必要予以说明。 花生原非我国内地所产,学界一般认为原产于巴西、秘鲁,早在明末清初即传入广东、福建一带,清朝嘉、道年间,江南数省已较为流行,但未大面积种植,早期记载多论及其药用价值,有“番豆”“长生果”、“长果”、“及第果”、“落花生”、“落花甜”等俗称。经中国传入日本后,称“南京豆”。鸦片战争前后,花生已传入山东,如道光(1830)年间《冠县志》,已记有落花生,道光(1838)年间《观城县志》则记有“落花甜”,道光(1845)年间《胶州志》卷十四谓:“落花生……东鄙种者尤广”;1869年《黄县志》记述落花生已较普遍种植。虽然现在已很难考证那时的花生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从连警斋的记述以及笔者所了解的一些情况看,那时这些江南和山东的花生,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花生还是大不相同。 连警斋记述说:“中国原有之花生,发源于江西省。盖赣州一带多沙地,故宜种之”。江西南城县志记载,华生在当地俗呼“番豆”,“又曰及第豆,及第者,及地也,言及地而生也”。“日本名南京豆,南京即中国之意,盖日本又得自中国也。然为体皆小,其形如豆”。 笔者近年曾到过江西,吃过几次江西的花生。那里的花生与南方一些省份的花生大致相同,果仁很小,虽说比豆粒大的多,但远不及现在蓬莱一带产的小花生大,更不用说大花生了。而且,感觉味道也远不如蓬莱一带的香甜,大致与山东济宁等地产的小花生差不多,但果仁比济宁、河泽、临沂等地的要小。笔者少时还曾见到一种小花生,老人说那是长生果,确乎是“及地”而生,叶梗不是直立,而是爬行生长,花生果仁如大豆粒般大小,三仁至六仁的居多,产量很低,不宜大面积种植。平时难得一见,总是在过年节时,炒熟与熟菱角等放在一起招待客人,或给小孩子做礼物。这种花生与上述连警斋所介绍的江西花生应为一类。至于今天江南的小花生是否是由此进化或杂交而来,广东、福建最初传入的花生到底什么样子,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山东有些地方的花生的具体情形,则有待方家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花生成为山东重要出口产品,却不是由这种花生发展而来,而是应归功于到蓬莱传教的美国北长老会牧师梅理士。 连警斋在编著《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时,曾主张“向中国所有花生贩子醵以巨资”为梅理士“立一铜像,以表彰之”。原因就是梅理士带来的大花生,几经繁衍,遍及山东各地,其后又“及于他省”,世人“徒知吃花生,而忘记赐我花生之人,是太无意识也”。并且说当时蓬莱人为了给这件事留个纪念,就为梅理士带美国大花生种来的那一年生的儿子梅赞文,起了个绰号叫“大花生”。“呼其名为大花生,所以不忘其惠也”(连警斋前揭书,第14页)。 有人说倪维思也是引进美国大花生的人,这恐怕没有依据,至多是他后来在烟台也种过花生而已。因为我们今天看不到倪维思本人和倪维思夫人的中英文记述,但连警斋在编写《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时,却大量引用了倪维思和倪维思夫人当时写的作品,他没有说倪维思在引进美国优良水果品种的同时也引进了美国的大花生,而坚持要为梅理士筹资竖碑,以表彰和纪念其引进美国大花生之功,当是有充分理由和根据的。我们今天没有凭据争相传说倪维思也引进了美国大花生,是不妥的。 关于梅理士引进美国大花生的时间,目前没有统一说法。一说是笼统指出梅理士看到登州海边多沙地,适合种花生,即劝农民种植,结果成功,传播开来后成为山东重要出口商品。一说是他1862年来时即带来了花生种,但没有更详细的内容。还有一说比较具体,认为是1882年梅理士从美国回来,“曾带来大花生一口袋,分与平度教友李正普,令之播种于地。翌年,特别繁殖,乃送一包来,请梅牧享受。梅牧复分之各处播种繁殖。不数年,已普遍山东,其后乃及于他省”。并指出“梅牧有一子,为带花生来之年而生者,名梅赞文,然人多呼其名为大花生”( 连警斋前揭书,第114页)。 查梅理士原本在上海数年,1862年7月从上海来登州时有两个孩子,都死于烟台至蓬莱的路上(当时流行霍乱),而且刚从上海来,又是7月份,在山东没有熟悉的人,不可能让人种花生,甚至没有花生可带,所以19世纪60年初代引进了美国花生一说,没有可信的依据,基本可以否定。海关统计资料表明,山东花生成批出口始于1891年,花生油批量出口则在十年以后(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统计资料》,对外贸易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39页)。而经查梅理士来中国一生共休假三次,分别为1869、1882、1892年。如果按照连警斋的说法,1882年当年不一定就种了花生,因为梅理士的继室夫人说梅理士1882年休假,显然1883年才能试种,1884年梅理士再分给人种,那得到1885年才有一定收获。如此反复扩大种植面积,到1891年,也才5-6年时间。考虑一种外国作物在当时条件下的引进繁殖和推广情况,并且由基督教徒散播,5-6年时间就达到批量由港口出口的规模,也不现实。所以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梅理士1869年回国休假时带来的花生,他这时已经在登州生活了7-8年的时间,既了解了当地气候土质,也有了可以信赖的教徒,从1870年开始试种,经20年时间传布开来,倒是比较实际。另外,据可靠英文史料,梅理士第一位夫人是1874年去世的,第二位夫人1884年才到登州,1887年创办了起喑学馆,1882 或1883年梅理士家根本不可能有生孩子一说,所以虽然连警斋言之凿凿,但时间肯定有误。到底梅理士何时引进了美国花生,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 梅理士去世后葬在蓬莱,现在蓬莱八仙渡还存有梅理士牧师的中英文双面墓碑。笔者不揣冒昧,建议蓬莱有关方面妥善保存。 梅理士夫人(Mrs. Ross McMaster Mills,梅理士原配夫人,时人称第一梅师母) 1862年到登州,1874年病故。身后留下四个年幼的子女,其中一个为聋哑儿。倪维思夫人曾用中文写成《梅莫氏行略》(上海美华书馆,1875年版),详细介绍了梅理士夫人的生平,可惜今天已难见到。 梅理士继室夫人梅耐德(Mrs. A. T. Miils, 时人称第二梅师母) 梅耐德原为美国纽约罗契斯特(Rochester)启喑学校教师,本名汤普森(Annette E. Thompson),梅理士博士再婚前曾将他的聋哑儿送该校接受训练。汤普森1884年到登州,同年与梅理士结婚,婚后中文名字梅耐德,于1887年和梅理士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登州启喑学馆,是中国现代聋哑人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898年,随起喑学馆迁烟台,长期从事启喑教育,并为全国各地培训了大量启喑教师,为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的发轫、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1926年退休,1929年病故。 神学暨法学博士狄考文牧师(Rev. Calvin Wilson Mateer, D. D., LL. D.) 1836年1月9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洲坎伯兰县(Cumberland Co. Pa.),一位普通农民的长子,1864年1月到登州,1904年随登州文会馆迁潍县,1908年,率圣经翻译委员会在烟台审定官话圣经,得腹泻病,初未注意,后拟返回潍县,途中曾赴青岛就医,不治,9月病故,葬于烟台长老会公墓。 狄考文身体强健,多才多艺,处事严谨果断,容不得在他看来不合规矩的事情,对所办学校学生要求尤为严格,时人送其绰号“狄老虎”。 狄考文虽然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却是中国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教育家。他所创办的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所谓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指包括外国教会、中国政府以及私人创办的大学在内的所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是西学东渐的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来华传教士率先在首批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兴办了小学、中学教育。第二鸦片战后的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中开明官僚主持兴办了旨在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先进科技的西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工艺学堂(1868年)、广东实学馆(1876年)、福州电报学堂(1876年)、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金陵同文电学馆(1883年)等。但是,普通的中小学教育,除了传教士开办的之外,依然阙如。登州作为第二次鸦片战后的通商口岸之一(后改烟台),自1860年起一些传教士陆续来到这里。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先来一步的南浸信会牧师海雅西夫妇曾经办过学校,但种种原因时办时停,一直没有成功。1861年到登州的美国北长老会牧师倪维思夫人,在1862年冬季创办了一所现代女子学堂,也是时办时停,成效不著(最后终于改为文会女校,才走上正轨)。1864年到登州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当年秋天即创办了登州蒙养学堂(登州文会馆前身),虽然早期很艰难,但却不仅坚持下来,而且逐步发展壮大,1877年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同时举行了首批毕业生典礼(一说1876年,实际上应为1876年底、1877年初之事,由于记载有阴、阳历之别,故有年分之差),因此,后来齐鲁大学的学生把这首批三名毕业生视为齐鲁大学首批校友。当然,这时的登州文会馆还只有中学程度,或有些课程高于一般中学(三位毕业生中有一位到杭州负责一所教会学校,该校比登州蒙养学堂早办20年,据说办得很红火;一位到烟台苏格兰长老会办的一所中学教书),但尚不具备真正大学水平。不过,翌年,狄考文即计划要在保留中小学的基础上,把登州文会馆办成大学,并制定了各种规章。1879年,狄考文利用回国休假之机,广泛游说,多方筹款,为办大学做准备。 1881年1月,狄考文回到登州,一边大规模加设大学课程,一边再次向长老会美国差回本部提出办大学的申请。1884年(一说1882年),美国长老会差回本部正式授权登州蒙养学堂办大学。1905年(一说1904年,事实是公历1894年底结束了在登州的教学,1895年初搬迁的),登州文会馆迁潍县,合并当时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开办的广德书院(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中的大学班,更名广文学堂,稍后成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即齐鲁大学的文理科(science and arts department,也称文理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文科、理科。当时医科在济南,神科在青州。1917年,广文学堂和青州的神学院迁济南,是为济南齐鲁大学的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后来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两个院,神学院独立出去,仍为三个学院)。 由上可见,登州文会馆才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它比号称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992年开始开设大学课程,1906年学校在美国注册,正式称圣约翰大学),即便从1884年算起(其实此前数年已开设大学课程),也早了8年;比号称中国政府办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1895年10月光绪皇帝诏准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996年正式创办,更名“北洋大学堂”,义和团运动期间成为八国联军兵营,1902年袁世凯奏请拨地重建,改名天津北洋大学堂),至少也早11年;比号称“最早的国立大学”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筹办,1902年正式开学),要早近20年。 据北京大学教授王忠欣在美国三年研究的结论,登州文会馆在成为大学以后,所开设的西方科学方面的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而社会科学方面的“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当时称为心灵学、是非学和富国策)”,则“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课程”。(王忠欣:《传教与教育》,网络版,第三章“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的产生” http://www.hleung.com/CS103/cs103ch2.htm)。如上所述,美国学者小海亚特也认为登州文会馆“几乎无疑是19 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后来中国政府办大学的情况,以及各省中高等学堂包括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聘用教师的情况,都证明了登州文会馆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既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也是最好的大学。 1898年清政府维新改革,创办京师大学堂,曾授权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字冠西)选任教师,丁韪良就选了8名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担任数、理、化各科教习,一人担任汉文教习。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创办的中国省级第一所现代大学——山东大学堂,即是由当时文会馆馆长赫士(狄考文1890始出任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馆长即监督一职由赫士接任)率领文会馆外籍教师和学生,仅用一个月时间完全按照登州文会馆的模式、规章创办起来的。结果,慈禧颁发诏令,命各省立即仿照山东举办新式学堂。一时间,文会馆学生供不应求,“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王元德、刘玉峰:《登州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刊行,第4页,)。“京师大学堂之外,全国各省(除贵州)的大学堂;工、农、师范学堂;上海,天津等地官办的格致院(科学院),南洋公学,北洋师范,江南大学等,以至保定武备学堂及师范学堂,奉天,云南讲武堂等,都聘有文会馆的毕业生。至于教会大学中,有文会馆毕业生任教的更占多数,其中如:张丰年在圣约翰大学任数理及天文学教授,成绩卓著,甚为学生所敬爱。但各省大学需要师资太多,文会馆毕业生数额有限,穷于应付,后来连肄业生也被延致。因此,对于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体制的建立,文会馆贡献很大”(于中旻:《狄考文与中国哈佛大学》,《翼报》 www.eBao Mongthly.com, 第四期) 。 作为一名传教士,狄考文早在他确立了到国外传道志向时,就曾坚定地表示:“我决意把我的一生献给中国,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他实践了自己的志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最后葬在了中国。在四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晚年他在一封信中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具有辉煌的前途。很高兴我有机会为她迈向辉煌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情”(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P.305,319)。 诚然,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那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决心向中国传布上帝之爱,带有浓郁的征服异教的宗教冲动,但也无需否认那时基督新教的海外宣教运动具有强烈的关切民生和人类所有民族进步的属性,尽管这一属性是基于所谓基督救世和上帝之爱。事实上,就狄考文一生来看,与其说其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上帝之爱,不如说他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除了办教育率先为中国引进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才之外,他还为本地商人设计制造或联系购置了煤球机、麻绳机、织麻袋机、打谷去壳机、磨麦粉机;购置和制作了大量现代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种实验设备;先后独自或督率他人译编各级各类现代学校教科书近30种,宗教著述近10种。中国文学界所熟知的世界著名汉学家、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主席马悦然(Goran D. Malmqvist),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他的老师、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则可说是通过自学狄考文的《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过了汉语言关的。狄考文主持翻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被海内外认为是最规范的白话即现代语言译本,其语言成就,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中国新文学起到了催化和示范的作用。因之,说狄考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毫不为过。 狄考文夫人(Mrs. Julia R. Mateer,狄考文原配夫人邦就烈,亦作邦就列,婚后中文名字狄邦就烈,或狄邦就列) 1837年生人,少时失去双亲,14岁偕妹妹寄居舅父家中,18岁开始自谋生计,25岁与狄考文结婚来登州,1898年在登州去世,享年61岁。 她一生在登州传教、办学,没有生育,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登州蒙养学堂和后来文会馆的学生们。有关资料显示,她很可能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入中国的人。据狄考文在大学和神学院的同学,也是他一生的好朋友,后来担任汉诺威学院(Hanover College)院长的费舍根据狄考文的通信和日记所写的《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一书介绍,登州蒙养学堂刚开办时,由于语言不通,先聘请中国老师教学,但不久狄考文夫妇就开始亲自上课,狄考文教算术,狄邦就烈“教授地理,向孩子们介绍中国以外的世界,开阔他们的视野。她每个星期还有三次特别难做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教孩子们唱歌”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P.136-137)。登州蒙养学堂创办伊始就上音乐课,这很可能与狄邦就烈青年时期就做过数年教师有关,这种情况在早期的教会学校中是很少见的。早期教会学校的办学目的,主要是培养宗教人才,虽然有些教会学校也学习唱歌,但尚未发现有像蒙养学堂那样的系统音乐教育,也没有见到比狄邦就烈编写的《乐法启蒙》(1872年初版,1879、1892、1907、1913年曾多次补编重印)更早的西方音乐教材。登州蒙养学堂的现代音乐教育,在清末新政改革时期废科举、大力兴办现代学堂的运动中,也还不是必修课,而登州早在1860年代中期就每周三次必修了,早于中国推广现代音乐教育40年。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登州蒙养学堂的音乐教育一直延续到文会馆时期,现存《登州文会馆志》中保留的一些该校校歌,都是文会馆的学生创作的五线谱曲,二、四部合唱歌曲,这说明登州文会馆的音乐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可以说独步当时中国音乐界。 狄考文继室夫人(Mrs. Ada Haven Mateer) 1900年到登州,1904年随狄考文和文会馆迁潍县,狄考文去世后长期在潍县长老会工作。 贝姑娘(Miss Patrick) 1864年到登州,1870年离开,去何地不详。 神学暨法学博士郭显德牧师(Rev. Hunter Corbett, D. D., LL. D.) 1864年初与狄考文等一起到登州,1864秋,迁至当时之珠玑村,1865年末迁烟台毓璜顶(亦作玉皇顶,而且是本来的名称。自长老会进驻之后,由于宗教的原因,改称毓璜顶,虽然一度受到官绅的强烈抵制,但终于还是相沿成习),1920年在烟台去世。 郭显德传教广泛撒网,颇有建树,初期遇有冲突,多能隐忍,且动辄以儒家道理与人理论,时人送其绰号“郭麒麟”。 郭显德夫人(Mrs. Hunter Corbett, 郭显德原配夫人) 1864年初与郭显德一起到登州,因无住处,先后迁珠玑村、烟台毓璜顶,1873 年在烟台病故。 哈丕森牧师(Rev. E. P. Capp) 1869年到登州,1871年病故。 哈丕森夫人(Mrs. M. Brown,狄考文夫人邦就烈的亲妹妹,结婚前中文名字邦玛吉,时人称邦姑娘) 1866年到登州,1871年与哈丕森牧师结婚,1885年病故。 邦玛吉一到登州,就立即在刻苦学习汉语的同时,帮助姐姐照料蒙养学堂,这时的狄考文还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办学上,他以为一个小学堂由他夫人和邦玛吉再加上一个中国教师就足够了。因此,常常外出旅行布道。《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的作者费舍,认为邦玛吉“在蒙养学堂创办初期,对蒙养学堂的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为了教学需要,她翻译了一部心算课本,在这方面,狄考文给予了帮助”。 邦玛吉的丈夫结婚当年就病故了,在丈夫去世以后,她又在登州工作了14年,于1885年也不幸病故。临去世前,在狄考文的鼓励下,把自己的“微薄积蓄捐献给了女子学校,用于校舍建筑,她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登州女子学堂”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P.143-144)。 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所谓登州文会馆在成为大学之前,“全部教职工只有4人,即狄氏夫妇、1名儒师和1名老媼司厨”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 马瑞森夫人(Mrs. M. E. Morrison,教内人称马师母) 1869年到登州,1870年离去,去向不详。 隋斐士牧师(Rev. J. Fisher Crossette) 1870年到登州,1872年迁潍县,1876年复迁济南, 1878年山东大灾荒时参加赈灾患饥荒热病,终身未愈,约在1905年前后去世。 隋斐士夫人(Mrs. Mary M. Crosserre,时人称隋师母) 1870年与隋斐士一起到登州,随之又先后同隋斐士一起迁潍县、济南,据有关史料推测,晚年返回美国。 医学博士柏德森(J. P. Patterson, M. D.,时人称柏德森大夫) 1871年到登州,设立诊所,主要为传教士及其家属看病,也为普通百姓看病,但当年即离去,去向不详。 柏森德夫人(Mrs. H. F. Patterson) 与柏森德同年到登州,同年离去。 狄克(E. S. Dickey,时人称狄克姑娘) 1873年到登州,翌年离去,去向不详。 医学博士卜立思(S. F. Bliss, M. D., 时人称卜立思大夫) 1873年到登州,继柏德森大夫经营诊所,但仅住一年多,翌年离去,去向不详。 邵牧师(Rev. J. M. Shaw) 1873年到登州,1875年病故) 邵牧师夫人(Mrs. M. H. Shaw,时人称邵师母) 1873年与邵牧师一同到登州,1884年于邵牧师病故九年后返回美国。 神学博士惠牧师(Rev. John Wherry, D. D.) 1878年到登州,1879年迁北京。 惠牧师夫人(Mrs. John Wherry, 时人称惠师母) 1878年与会牧师一同到登州,翌年同迁北京。 医学博士克利斯(Miss A. D. H. Kelsey, M. D., 时人称克利斯教士或克利斯姑娘。“姑娘”或“教士”,均为当时人对差会单身女工作人员的称呼。) 1878年到登州,在东大寺设立医院(实际上也还是诊所性质,但时人称之为医院),为传教士及其家属和当地百姓看病。办院期间,雇用一名中国助手,据说“见习急救,亦能行医,女士去后,彼则自设医肆卖洋药以西法治病,利市三倍”(连警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37年版,第176页)。 1882年底,不知何故迁日本。 医学博士司密斯(Horace R. Smith, M. D.) 1881年到登州,翌年离去,去向不详。 狄莉莲(Miss Lillian Mateer,狄考文最小的妹妹,时人称狄姑娘) 1881年与三哥狄乐播一起到登州,在登州文会馆女校教书。1883年与美国上海南浸信会的萨缪尔•沃克牧师(Samuel Walker)结婚,去上海一所南浸信会学校教书。后因沃克牧师的健康关系,随丈夫返回美国。 良约翰牧师(Rev. J. H. Laughlin,亦作劳福林、梁约翰) 1881年到登州,在这里学习汉语和布道。1883年与狄乐播一起在潍县城郊建了一处布到站,作为从烟台和登州启程巡回布道的据点,后长期在各地巡回布道,1891年赴济宁建立新布道区。 神学博士狄乐播(Rev. R. M. Mateer,D. D.,狄考文三弟) 1881年同妻子和小妹狄莉莲一起到登州,随大哥狄考文学习汉语和布道,妻子到登州当年病故,他本人于1883年迁潍县。 神学博士赫士牧师(Rev. W. M. Hayes, D. D.) 1882年到登州,以登州为基地在胶东栖霞、黄县、掖县等地传教,同时任教于登州文会馆。1891—1895年间先后任上海广学会书记、会长,首创“化学”学科名词。1901年应山东巡抚袁世凯聘,赴济南任山东高等学堂总教习,创办《山东时报》。1904——1919年任齐鲁大学神学院教授。1919年创办华北神学院, 1922年迁往滕县,规模声势颇为可观。日本大举侵华后,将其逮捕与其他英美人士一起关押在潍县集中营。后因拒绝作为战俘交换,坚持把名额让给年轻人,死于集中营,享年近90岁。一生著述颇丰,编译《天文揭要》、《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等十几种教科书和著作,对中国尤其是现代教育贡献颇多。 赫士夫人(Mrs. W. M. Hayes) 1882年同赫士博士一同到登州,后又一同迁济南、藤县。1841年,与丈夫一起被侵华日军羁押于潍县集中营,晚年情况不详。 医学博士聂会东(James Boyd Neal, M. D.) 1883到登州,续办医院,兼办药房,并培养了6名学生,日久皆能独立治病,这些学生后来随他一起去了济南。蓬莱长老会医院在他主持期间,“日渐发达”,本来他有意在文会馆内开办医学专业,但设备及其他条件限制,未能如愿,遂选择了省城济南作为其施展才华之地。到济南后,负责美国长老会在济南的医疗事业,后出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1919 年任齐鲁大学校长,1922 年因病返回美国。 聂会东夫人(Mrs. James Boyd Neal) 1883年与聂会东一同到登州,1990年迁济南。 海尔济牧师(Rev. George Hays, 又作海斯,赫士,均系音译。海尔济为当时中文名字,其姓Hays与上面的赫士—Hayes不同) 1888年到登州,1890年迁烟台,因他主张利用当地丰富的水产品及水果搞加工业,引起其他传教士不满,被认为与传教士身份不符,报负难以施展,三年后返美。 海尔济夫人(Mrs. George Hays,时人称海师母,郭显德女儿,中文名字郭范霓) 出生于中国,少时长于中国,后回美国读书。1888年与海尔济牧师一同到登州,在登州文会女校教书,同时教女生以及乡村妇女织花编,是将西洋花边编制技巧和样式传入中国并试图使之产业化的第一人。1894年,随丈夫海尔济返回美国。 哲学博士伊维廉牧师(Rev. W. O. Elterich, PH. D.) 1889年到登州学习汉语,并从登州出发,在各地巡回布道,1891年与其他传教士一起,开辟了沂州布道区,随即迁居沂州。 伊维廉夫人(Mrs. W. O. Elterich) 1889 年同伊维廉牧师一起到登州,1891年迁居沂州。 富济克牧师(Rev. E. G. Ritchie) 1889年到登州,翌年病故。 富济克牧师夫人(Mrs. E. G. Ritchie) 1889年与富济克牧师一同到登州,后来再嫁凌格尔牧师。 纪力宝牧师(Rev. Charles Killie) 1889年到登州,学习汉语和布道,1890年底赴沂州开辟新布道站。 纪力宝牧师夫人(Mrs. Charles A. Killie) 1889年与纪力宝牧师一起到登州,翌年底迁沂州。 费惜礼牧师(Rev. J. A. Fitch) 1889年到登州,学习汉语,熟悉布道环境,1891年迁潍县。 费惜礼牧师夫人(Mrs. J. A. Fitch) 1889年与费惜礼牧师一同到登州,两年后随丈夫一起迁潍县。 怀姑娘(Miss Fannie Wight ) 1890年到登州,当年迁潍县,1892年病故。 医学博士寇得满(Robert Caltman, M. D.,时人称寇大夫) 1890年到登州,继聂会东经营登州长老会医院,1893年去天津,后又转迁北京。 寇得满夫人(Mrs. Robert Caltman) 1890与寇得满一起到登州,三年后先后随丈夫迁天津、北京。 顾牧师(Rev. S. B. Groves) 1891年到登州,1894年迁烟台。 顾牧师夫人(Mrs. S. B. Groves) 1891年到登州,1894年随丈夫去烟台。 莱恩牧师(Rev. William Lane, 时人称蓝牧师) 1891年到登州,学习汉语,巡回布道,1893年去济宁开辟新布道区。一说1891、另说1892年去济宁开辟新布道区,实际上那时只是随良约翰到那里巡回布道。正式迁居应是1893年,1897年病故。 莱恩牧师夫人(Mrs. William Lane) 1891年与莱恩牧师一同到登州,1893年随丈夫迁居济宁,丈夫去世后返回美国。 范斯柴科医生(I. L. Vanschaick ,又作J. L. Van Chorick ,未知何是,时人称范大夫) 1891年到登州,学习汉语,1892年迁济宁,1898年病故。 范斯柴科医生夫人(Mrs. I. L. Vanschaick,时人称范师母) 1891年与范大夫一起到登州,1892年同去济宁,后在济宁病故。 薛姑娘(Miss Mary Snodgrass) 1893年到登州,据《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的作者连警斋称“常住登州”,但后来1936年前后时,登州已无此人,去向待考。 医学博士慕维甫(Walter F. Seymour,M. D., 又作慕杂甫) 1893年到登州,继寇得满之后经营长老会医院,并开办医校,训练学生和看护,医院较聂会东时又有所发展。1918年赴济宁长老会工作,1928 年被国民党军杀死。 慕维甫夫人(Mrs. Mary Ada Seymour) 1893年与慕维甫一起到登州,1918年随丈夫迁济宁,丈夫被杀后情况不详。 神学博士文约翰牧师(Rev. John Prescott Irwin, D. D.) 1894年到登州,一直在这里从事传教、教学工作,约于1936年前后退休返回美国。在此期间,他先于登州文会馆旧址开办文会中学、文会小学,各种规制一如狄考文时代,后来中学又添设英文班以符合民国新学堂课程要求,附设师范班为贫穷家庭孩子不能升大学者谋生活出路。 文约翰牧师夫人(Mrs. Murtha A. Irwin) 1894年与文约翰一同到登州,在文会女校教授英文和声乐,在城里及乡村妇女中间布道,1935年病故。 利姑娘(Miss R. Y. Miller ) 1895年到登州,1900年嫁其它教派牧师后离开登州。 卫礼大夫人(Mrs. M. G. Wells,时人称卫礼大师母) 1895年到登州,据推测应为到这里来学习汉语,因为她没有和她的丈夫一起到登州,她到登州时丈夫留在了烟台。其具体工作性质不详,从其它资料推测,似为教会一般工作人员,或是教会学校的教职员。1903年与后到登州的丈夫一起迁至烟台。 医学博士陆义思(Charles Lewis, M. D.) 1896年到登州,学习汉语并参与长老会医院工作,1898年迁济南。 陆义思夫人(Mrs. Charles Lewis,时人称陆师母) 1896年与陆义思一同到登州,翌年病故。 路思义牧师(Rev. Henry Luce) 1897年到登州,学习汉语,并在登州文会馆任教。1904年文会馆迁潍县时,一同迁居潍县。时值中国内忧外患、列强环伺,有识之士呼吁改革,以图富强。路思义认为应在中国加大大学教育力度,培育引领20世纪一代精英。为此,他多方工作,促成了美国北长老会、英国浸礼会和安立甘会联合举办齐鲁大学,并为此忍痛舍弃心爱的教职,先后于1906、1912年返回美国花数年时间募集捐款数十万美元,奠定了齐鲁大学发展的稳固基础。虽然先后出任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副校长,但长期为在中国办高等教育返美筹集资金,并未在这两所大学任教。1927年,由于长期奔波,58岁的路思义身心疲惫,为重执教鞭,入学校进修,后留在美国任教,1941年病逝。 路思义夫人(Mrs. Elisabeth Rose Luce,时人称路师母) 1897年与路思义一同到登州,1904年随丈夫和登州文会馆迁潍县,但和路思义一样,并未在潍县久留,当路思义长期在美国筹集资金时,估计她即返美,具体情形待考。 卫礼大(Mr. Mason Wells,时人称卫礼大先生) 1895年到烟台,1899年来登州与夫人团聚,具体工作不详,待考。1903年与夫人一起转至烟台。 卫礼士(Mr. Ralph C. Wells, 时人称卫礼士三先生) 1902年到登州,1904年随文会馆一起迁潍县。 上述有卫礼大先生,两人一个姓,但不知是否兄弟,待考。鉴于无论烟台还是后来的潍县,长老会都没有另外姓Wells的,而且迁潍县后,因为没有同姓的,即不再称“卫礼士三先生”。在登州时这样称呼,可能当时为区别记,根据来的早晚或年龄大小加“大”、“三”以利辨识。另,这一位Wells,与上述Wells,一样,时人都称其为先生,看来也不是传教士,可能为教会一般工作人员或教会学校教师。 柏尔根牧师(Rev. Paul D. Bergen) 1901年到登州(有误,待考),任教登州文会馆,并接替赫士出任监督即校长一职,1904年随文会馆一起迁潍县。文会馆更名为广文学堂、齐鲁大学(初称山东基督教大学)文理学院后,继续担任监督、院长之职。1915年病逝于潍县。现在山东大学西校区(原齐鲁大学,后来的山东医学院、山东医科大学)校园内,仍有保存完好的“柏尔根楼”(原齐鲁大学的化学楼) 柏尔根牧师夫人(Mrs. Paul D. Bergen) 1901年与柏尔根一同到登州,1904年随丈夫和文会馆一起迁潍县。后来情况不详,待考。 伊爱德(Ida J. Emerick) 1901年到登州,原为烟台内地会成员。1898年嫁长老会怀卡文牧师(Rev. Calvin Wight)后,随丈夫到济南,1899年,怀卡文病故,处理完丈夫后事,正值义和团运动,随其他传教士一起避难,1901年到登州参加长老会工作,时人称“怀师母”(Mrs. Ida J. Emerick Wight)。从此,一直在登州负责文会女校,并兼做传道工作。在她主持文会女校期间,将察院后的校址迁至东关,规模扩大,学生常年住校生增至100余人。1912年学校迁址东关时,登州教会、烟台美国领事、烟台美国长老会及英国浸礼会代表、登州地方政府官员等,聚集召开隆重庆祝大会。此后,伊爱德在登州文会女校从事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也经常率领弟子到乡村传道,直至1935年退休,把丈夫去世后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登州女子教育事业。退休后的情况不详,待考。不过,伊爱德为加拿大人,与怀卡文结婚后脱离了内地会,结婚一年丈夫即病故,此后终身为美国长老会工作,无子女,很可能留在登州,并像其他英美等国的传教士一样,为后来日本侵略军当作战俘虏至潍县集中营。 麦牧师(Rev. C. P. Metzler) 1903年到登州,翌年返美。 郝艾斯(Miss Charlotte M. Howes,时人称郝教士、郝大夫) 1904年到的登州,1906年迁潍县。从有关资料看,郝艾斯不是医生,而是当时西方的护士,到登州来应该是一边学习汉语,一边见习医护工作。 费明珠教士(Miss Margaret A. Frame) 1910年到登州,单身女传教士,有资料说其常住登州,但具体在登州呆了多少年,目前尚不得而知,待考。 道阿玛教士(Miss Alma B. Dodds) 1910年到登州,单身女传教士。据称她到登州来之后,“掌理医院事务,兼开护士训练班,男女并收,成绩甚佳,虽有许多离此而去自谋生活者,然所留之看护士,皆是能手,有入医科大学资格”。从道阿玛初来为单身女士、时人称其为“教士”及“姑娘”的情况看,在熟悉了汉语以后,办护士训练班很有成绩,起码需要四五年的时间。从上述慕维甫直到1918年才离开登州到济宁的情况看,蓬莱长老会医院民国初期尚存,应当有医生和护士在这里工作。据称道阿玛到登州后,这里的长老会医院已经先后得到美国塞维朗斯(L. H. Severance)先生和顾德(Miss Helen Gould)小姐捐助11500元美金,院内可容纳病人40,“冬有汽炉(即今天所谓暖气),夏有风扇”,还设有手术室和传染病隔离室(连警斋前揭书,敌179-180页)。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医院可说是有模有样了。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不见登州长老会医院以及医护人员的记载。究竟登州长老会医院何时解体、道阿玛等医护人员的去向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挖掘史料,弄清真相。 巴堪朴牧师(Rev. Otto Braskamp) 1911年到登州,何时离去不详。 巴教士(Miss Christian J. Braskamp) 1911年到登州,何时离去不详。 苏美丽(Miss Mary J. Stewart) 1911年到登州,1913年迁沂州府,直到1930年代中期,仍在那里的长老会工作,始终单身。日本侵略者侵占山东时,如未撤离,则应沦为战俘关进潍县集中营。 富撒拉(Miss Sarah Faris) 1911年到登州,一直在登州长老会工作,1930年代中期,担任登州长老会主席。后来情况不明,待考。 文学硕士武 文(Arther C. Owens) 1921年到登州,美国长老会登州差会执行委员,兼任登州文会中学教师。 武拉结(Rachel Wood Owens) 武文的妻子,与武文同年到登州,负责妇女及儿童工作,兼任登州教会书记(秘书)。在登州期间,武氏夫妇育有五个子女,依次为:武大卫(David Arther Owens,1922年生)、武马利(Mary Elizabeth,1924年生)、武喜乐(Wallace Wood Owens,1928年生)、武安乐(Ann Louise Owens,1930年生)、武长乐(Boone Bailey Owens,1932年生)。 武氏一家,日本侵略军占领山东时如果未撤离,亦应当作俘虏被关进潍县集中营。当时潍县集中营男女老少皆为俘虏。 文学硕士、神学博士嵇乐实(Harris G. Hilscher M.A., S. T. D.) 1923年到登州,在登州做传教工作。很幸运,1937-1938年,按规定回美国度假,是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又回来工作,待考。 文学硕士嵇乐德(Gladys Janes Hilscher) 嵇乐实夫人,与嵇乐实同年到登州,在登州文会中学教书,兼任登州教会司库。1837-1838年携丈夫在美国度假,后来情况待考。 司碧珂(Margery Speake) 1931到登州,单身女士,专任登州文会中学教师。1938年返美度假,后来情况待考。 参考文献: 1、连警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37刊行。 2、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刊行。 3、《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刊印。 4、阿姆斯特朗:《山东》(Alex. Armstrong, Shantung (China) 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a sketch of its missions, and notes of a journey to the tomb of Confucius,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1)。 5、季理斐编:《中国差会年鉴》(1910、1913、1915),上海:广学会(D. MacGillivrary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6、费舍 著:《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 7、法思远主编:《中国圣省山东》(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Compiled and Edit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8、阿美德编:《图说烟台通志》 (A. G. Ahmed Compiled, Edited And Published, Pictorial Chefoo, 1936)。 9、1860—1937山东差会历年汇存: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会议记录,1937年,青岛(Bridging the Years Shantung Mission 1860-1937: Minutes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 10、小海亚特著:《圣使荣哀录——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郭大松: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